| 查看: 837 | 回复: 10 | |||
| 当前主题已经存档。 | |||
Platinum木虫 (正式写手)
|
[交流]
【其他】郭可信:准晶与电子显微学
|
||
|
郭可信,著名物理冶金学家、晶体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瑞典皇家工程科学院外籍院士。我国电子显微学泰斗。早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后留学瑞典,1956年回国。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瑞典皇家工学院技术科学荣誉博士,瑞典皇家工程科学院外籍院士,日本金属学会荣誉会员。在科研工作中,为我国材料科学、晶体学、电子显微学的发展培养出一批优秀人才。其中已有2人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下面是其科学自传: 《准晶与电子显微学》 略述我的研究经历 郭可信 一. 开场白 1993年对我来说可能将是一个值得纪念的一年。首先我出任亚太电子显微学会联合会主席、任期四年。其次,我们的准晶研究得到国际学术界的承认,被邀请在八月下旬在北京召开的第16届国际晶体学大会作准晶特邀报告。还将主持八月底在承德召开的国际准晶学术讨论会。 这首先要归功于一批优秀学生,前后约有三十位硕士、博士研究生从事准晶研究。他们发愤图强,刻苦钻研,接连发现Ti2Ni二十面体对称准晶(与Ti2Ni立方相共生),八次对称准晶(与-Mn结构共生),还有NiV十二次对称准晶(与sigma相共生)。张泽、王大能、王宁、陈焕因此先后荣获第1及2届吴健雄物理奖,五次对称及Ti2Ni准晶的发现还获得1987年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何伦雄首次生长出AlCuCo十次稳定准晶并长出毫米级单晶,或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二等奖。这些有创造性的论文自发表以来已被引用近百次。此外,张洪等在十次准晶的近似晶体相结构及生成规律方面做出优秀成绩,获教委1992年自然科学一等奖。 在稳定准晶相发现之前,准晶主要是通过急冷获得的,晶粒一般都是微米量级,而且一般是几个相共生。对这些共生的微晶传统的结构研究方法如X射线衍射就显得无能为力,而用聚焦电子束成的显微像及电子衍射却得以充分发挥其威力,几乎所有准晶合金都是用这一实验方法发现的。 我有幸在1947-56年间在国外学习工作时就与合金结构和电子显微学打交道,1956年回国后又一直断断续续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因此能在1982年安装一台JEM200CX电镜及后来在北京安装两台Philips电镜后率领一批新生力量在合金结构及准晶研究中自由驰骋、左右逢源,发现了一批准晶合金及多种准晶结构。四十多年前播下的种子,四十年后才收成。时间可能长了一些,但是由于是丰收,这还是值得的。 |
» 猜你喜欢
 过年走亲戚时感受到了所开私家车的鄙视链
已经有9人回复
过年走亲戚时感受到了所开私家车的鄙视链
已经有9人回复
 体制内长辈说体制内绝大部分一辈子在底层,如同你们一样大部分普通教师忙且收入低
已经有6人回复
体制内长辈说体制内绝大部分一辈子在底层,如同你们一样大部分普通教师忙且收入低
已经有6人回复
 今年春晚有几个节目很不错,点赞!
已经有10人回复
今年春晚有几个节目很不错,点赞!
已经有10人回复
 情人节自我反思:在爱情中有过遗憾吗?
已经有10人回复
情人节自我反思:在爱情中有过遗憾吗?
已经有10人回复
 基金正文30页指的是报告正文还是整个申请书
已经有5人回复
基金正文30页指的是报告正文还是整个申请书
已经有5人回复
» 本主题相关商家推荐: (我也要在这里推广)
Platinum
木虫 (正式写手)
- 应助: 2 (幼儿园)
- 贵宾: 0.1
- 金币: 2219.3
- 红花: 3
- 帖子: 383
- 在线: 96.6小时
- 虫号: 134481
- 注册: 2005-12-15
- 专业: 凝聚态物性I:结构、力学和
|
二.与金相权威决裂 我在1946年夏从浙江大学化工系毕业后就赶上了公费留学考试,由于不想学造纸(化工方面唯一的报考专业),就转行搞冶金。在我之前就有不少浙大化工系毕业的学生这么做了,因为我们的化学基础好,特别是物理化学,考试占便宜。我的物理化学考的还不错,可是无机化学就砸锅了,因为有一道题(20分)要列出十种金属矿物名称,我除了黄铁矿、赤铁矿、褐铁矿外其它都不知道。当年秋后发榜,我居然还榜上有名,去瑞典学冶金。我对此完全是外行,去了重庆最大的大渡口钢铁公司实习了一个月,那里有一座高炉是1938年武汉沦陷前从汉冶萍钢铁公司拆运来的,有两座20吨平炉,现在看来小的可怜,但是那时这是大后方最大的。在那见到才从美国回来的周自定工程师(解放后在东北工学院任冶金系主任),他带回来一本才出版的Open-Hearth Steel Making,用物理化学原理分析炼钢过程中的钢渣反应。我第一次接触到这门三十年代兴起的化学冶金学科,非常兴奋。 瑞典是以优质合金钢著称于世的,特别是SKF的轴承,二次世界大战时盟军曾派潜水艇去瑞典西海岸偷运瑞典轴承,还有诺贝尔家族独占全部股份的Bofors钢厂大炮。我1947年秋天到了斯德哥尔摩,才知道只有瑞典皇家理工学院有冶金系,也只有三位教授,一为教冶金,一位教金相,一位教轧钢。我说明想学合金钢,就被分配到金相教授A. Hultgren那里,从此进入四十年代才兴起的物理冶金的门槛。 如果说化学冶金主要是在德国兴起的,那么物理冶金则主要是在美国兴起的,那时美国的最有名的物理冶金学家主要集中在MIT,Carnegie IT及芝加哥大学金属研究所三个学府。MIT的M. Cohen主要从事马氏体的相变研究;Carnegie的R.F. Mehl(二次世界大战负责军工研究,少将军衔)主要研究奥氏体等温转变,引入德国学者的晶核生成与长大理论研究相变(现在Carnegie-Mellon大学校园内还有他的铜像);芝加哥金属研究所由二次世界大战负责原子弹研制中的材料问题的英国人C.S. Smith主持,他本人研究晶粒晶界及冶金史,更重要的是网罗一批物理学家,如Zener,Barrett,葛庭燧等,研究金属的物理问题(Zener曾在二次大战中在美国水城兵工实验室带领一批杰出的青年物理学家Turnbull(五十多卷固体物理丛书的主编),Fisher,Hollomon等搞炮钢的相变及回火脆)。英国的物理学家那时的兴趣集中在位错,带头的是N.F. Mott,C. Frank,Orowan(位错的发明人之一,他在三十年代在德国找不到工作,回到匈牙利赋闲,就琢磨起金属的强度为什么比物理强度低的多,从而想到位错。他认为一个人一天忙于工作,很难有所发现。他还提到位错的另一位发明人G.I. Taylor,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在国防科研部门搞流体力学,战后闲得无聊,也搞起位错来)。位错的另一位发明人是匈牙利的青年物理学家Polany,他本想跟因发明用铂作催化剂在高温高压下人工合成氨而得诺贝尔化学奖的Haber工作,没想到Haber很骄傲,拒之门外(现在德国的电子显微学研究中心就设在柏林的Fritz-Haber研究所内)。他只好在柏林找一份X射线研究的工作,接触到六方对称的锌在范性形变中产生的滑移及织构。 我是在山沟里油灯下念的大学,初到未受战火波及繁荣富有的瑞典,连实验室煤气灯都不知道怎么点,受到一个英国实验员的嘲笑。外国有一句成语,“笑到最后的才是最好的”,那小子到老还是一个实验员,我这个土包子没几年后就当了研究员。不是他素质不如我,而是他没有抱负,没有理想,而我是发愤图强,要为中国的科学繁荣贡献一份力量。我很快就被金相显微镜所显示的金属微观组织结构的大千世界迷住了,如饥似渴的学习Masing著的“三元系相图”这本书。Masing原是西门子公司的实验室主任,战后是哥丁根大学的金属学教授,发明了碳管炉(直接通过大电流产生高温,西方称为Tammann炉)用以冶炼合金,带领一批学生和外国进修学者不到几年研究了几百种二元合金相图,找出合金规律,奠定了金属学的基础,德文Kunde就是知识、学问的意思。他的相图只是大体轮廓上正确,细节上错误不少。但是由这几百个不很准确的相图他找出不少有规律性的学问。与他同时有两位英国学者花了十年功夫,反复推敲,测定了Cu-Zn和Cu-Sn相图,几十年后还基本正确。一种是大刀阔斧,一种是精雕细刻,各有千秋,两种作学问方法都对科学发展有贡献。到底哪一种更好?见仁见智,其说不一,恐怕两者都需要。日本东北大学增本健(S. Masumoto)领导的准晶研究组(包括台湾学者蔡安邦)的工作作风就属于前者,大量配合金,终于发现Al-Fe-Cu,Al-Mn-Pd等一系列的稳定的二十面体准晶,现在成为二十面体准晶研究的主流。他在非晶态合金研究方面也是如此,发现了一批有实际应用价值的铁基磁性合金,在不到五十岁就被选入日本学士院(相当于我国的科学院,但学士名额仅一百人),可谓难能可贵。我们在他们的工作启发下发现了稳定的Al-Co-Cu及Al-Co十次对称准晶,从而在十次对称准晶研究中起了带头作用。Metallkunde的俄文译成Mettalobugenue,中文的金属学是从俄文转译过来的。1956年制定12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时,需要大量金属学人才。当时误译为金属物理,因此在17所大学建立金属物理专业,与工厂需要的人才不对口,直到八十年代才得到纠正。英国人叫金相,美国人叫物理冶金,大同小异。一个名词的译名不当,竟造成这么大的影响。Tammann的学生中有日本的Honda(本多光太郎),后来成为日本金属学的鼻祖及仙台东北大学校长和著名的金属研究所所长。第一个测定单晶磁化曲线的茅诚司(S. Kaya,后来成为东京大学校长,日本学士院院长,中日友好协会会长)也是他的学生。仙台东北大学一直是日本的金属研究中心。中国最早从事金相学研究的是周志鸿先生,他在1926年美国哈佛大学在金相大师Sauveur指导的博士论文就发现了针状铁素体,这是贝氏体的前奏。从日本学成回来的陆志鸿先生在30年代末,40年代初,就在一些大学讲授金相学,并写了一本教课书,后来他到台湾大学执教,在台湾创办了金属学会。我为在物理化学教科书中学到的非常简单的“Gibbs相律”竟能解释千变万化的合金相变而异常兴奋,日以继夜地工作、学习,不到一年我读了当时能找到的金相专著和几百篇文献,并成为金相权威Hultgren唯一的由大学支付工资的研究助教,管理他的奥氏体恒温转变组,研究合金元素对奥氏体转变的影响。同时我不满足于金相观察,并开始阅读X射线晶体学书籍和合金碳化物的X射线粉晶分析。 Hultgren在二十年代末在著名的柏林高工学的金相学(他的老师是Hannemann,在三十年代初著有钢铁金相图谱8册。日本人大量影印,现在沈阳金属研究所还存有从日本人手中(可能是长春的大陆研究所)接收下来的这部传世名著),属于那一代的靠金相观察和逻辑思维进行全部研究工作的人。他最出名的成就是研究钢锭凝固过程中气泡的形成及逸出以及由此造成的偏析,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生产问题,但是研究手段非常简单,用一个十几倍的放大镜进行宏观组织结构观察就行了。他把钢厂生产的上百个钢锭纵向刨成两半,进行观察,然后再横向锯成若干段,得以完成他的巨著。他的干劲越大,成材的钢锭越少,那个钢厂不得不请他离开,去当金相学教授。他就凭这些工作当上了赫赫有名的ASM(American Society for Metals)的荣誉会员。他不但保守,而且专横,是一个名符其实的暴君。随着我对X射线晶体结构研究兴趣的增长,我们之间的矛盾也就加深了,终于在1950年我当面对他说了“我不相信你那一套”有关合金元素影响奥氏体相变的自相矛盾的说法,放弃了三年多的研究成果,在读的学位,以及固定的工作,一走了事。我当时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敢于和这个大权威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可能是我认为学术问题就应泾渭分明,不能含糊,合则留,不合则去。 这件事好像我是输家,工作、学位、到手的论文都完了。其实不然,我换来的是学术上的彻底解放,完全自由。在1951年,我得到了瑞典钢铁协会的资助,立了一个“合金钢中的碳化物”课题,自己当家作主,每天从早八点到晚十二点,有时还雇一两个实验员帮助我做实验。我心情舒畅,才智和干劲得以充分发挥,此后每年都发表3-5篇学术论文。到1956年回国时已经有二十多篇文章,在1956年出版的德文“合金钢手册”一书广泛引用了我的研究成果。 只有与旧的研究课题、旧的学术思想决裂,才能有所作为。我后来还用传统的金相方法研究-铁素体的转变这个过去很少研究过的课题,很快在合金含量高的不锈钢、耐热钢、高速钢中发现了不少新现象,写了五篇论文,成为这方面的奠基工作。 三十年后,瑞典皇家理工学院的教授会在1980年授予我技术科学荣誉博士学位,那时国际冶金界得此殊荣的不过三、四人,其中有前面提到过的MIT的M. Cohen及英国的位错权威A. Cottrell。这也可能是他们觉得过去对我不公平,予以补偿。可惜那时Hultgren已过世,我没能和他再争论一番。 我从这一段经历得到的启发是: 1. 只有不断更新学术思想,掌握新的实验技术,才能在科学研究中有所发现。死抱住老课题、老一套,很难有所作为。 2. 这样做有时就难免与老板发生矛盾,因为有的老板迷恋过去成就舍不得丢掉原有研究基础。随着青年人业务逐渐成熟,老板的学术地位在青年人眼里逐渐下降。我主张据理力争,当然不一定吵架,只有自己骨头硬才能赢得别人的尊重,唯唯诺诺是没有人看得起的。我这几年在瑞典跑来跑去,不少老熟人还提起当年我与Hultgren争吵事,不无称慕之意。 3. 我也老了,就应知趣,不要当老保守,死顽固。千万不能熬到当婆婆的份上就忘了当媳妇的苦楚。应当鼓励青年人标新立异、敢说敢干。 |
2楼2009-05-28 09:53:46
Platinum
木虫 (正式写手)
- 应助: 2 (幼儿园)
- 贵宾: 0.1
- 金币: 2219.3
- 红花: 3
- 帖子: 383
- 在线: 96.6小时
- 虫号: 134481
- 注册: 2005-12-15
- 专业: 凝聚态物性I:结构、力学和
|
三. 在X射线合金结构研究中自由驰骋 从1951年到1953年,我就转到Uppsala大学无机化学系从事用X射线衍射方法研究合金结构的工作。一来我对用X射线衍射方法研究结构感兴趣,自学了Guinier,Buerger,Barrett,Bunn,Taylor等的名著。原子位置稍有变动,衍射强度就有明显变化,完全为这门严谨的科学所倾倒。二来Hägg教授在三十年代研究碳化物、氮化物时总结出(后来称为Hägg's Rule)如间隙原子(C、N、B)与金属原子的半径比小于0.69,间隙相就有简单结构(如面心立方,六角密堆),否则就会出现复杂结构。Hägg是一位学识渊博、为人正直的长者,深受学生及同事的尊重。他是Uppsala大学无机化学教授,早期的学生都有出色的工作,如R. Kissling的硼化物及钢中夹杂的研究,A. Magnéli的金属氧化物缺陷结构的研究。后来得诺贝尔化学奖的Tiselius当年也申请过这个教授位置,那时他没竞争过Hägg。Uppsala是一座宁静的大学城,也是历史上的故都,这几年我在这里过得很愉快,研究工作进展也很顺利。到那不久,我就发现了一种新的MoC结构,这是我做的第一个晶体结构测定,尽管比较简单,也算一个新发现。与Hägg合写一篇短文投Nature,在1952年刊出,第一炮总算打响了。 我在皇家理工学院做钨钢的奥氏体恒温转变时就发现在淬火后最先析出的钨碳化物是W2C,而不是一般认为的高速钢碳化物Fe3W3C=M6C。后者在高速钢(刀具高速切削升温到暗红色)中大量存在,误认为是高速钢红硬性的原因,因此称为高速钢碳化物。这种看法显然是错了,红硬性是由W2C析出产生的。到了Uppsala,我用那里的Guinier聚焦相机得到更可靠的证据,在1952年发表了一篇学术论文“Carbide precipitation, secondary hardening, and red-hardness of a hot-working steel”(Research, Vol.5, p. 339)。后来在1953年又发表了一篇长文,讨论的是高速钢中的碳化物与红硬性。接着又研究了Fe-Cr-C,Fe-Mo-C,Fe-W-C,Fe-Mn-C,Fe-Cr-W-C系中碳化物析出过程,分别写成论文发表。在Fe-W-C一文中弄清了六角密堆W2C转变为单胞参数为11.06埃的面心立方Fe3W3C的过程。 Fe3W3C的晶体结构是Hägg的同事G. Phragmén首先确定的,我在那工作一年多,一连发现许多合金碳化物,如Nb3Cr3C,W3Mn3C等,都有相同的结构,在1953年写了一篇“The Formation of Carbides”,在Acta Metallurgica上发表(Vol. 1, p. 301)。碳化物是晶体学名,高速钢碳化物是冶金学名,都指的是Fe3W3C一类碳化物。大约在同时美国科学家在一系列Ti合金相(如Ti2Ni,Ti2Co,Ti2Fe)中发现有与相同的晶体结构,只是其中无碳就是了。Ti2Ni就是后来张泽等发现二十面体准晶的合金,而立方-Ti2Ni相与准晶共生。在相的单胞中有96个原子,一半处于二十面体中心,都有一个五次轴平行于[110]。这是在急冷Ti2Ni合金找到二十面体准晶的晶体学基础。借此声明,张泽是在1984年底在这一合金中发现了五次对称电子衍射图,1985年2月在上海硅酸盐所得出二十面体对称,那时已见到Shechtman的文章了,我们晚了一步。 1955年在加热一个含钨的高碳钢到过烧状态,晶界有少许熔化,冷却后发现一个具有-Mn结构的新相。这是意想不到的,因此写了一篇“New intermetallic phase in a burnt tungsten steel”,投Trans. Amer. Inst. Min. Engrs.。文章发表时(1956, Vol. 206, p.97)我已经回到国内了。当王宁等在CrNiSi合金中拍出八次对称准晶及共存的点阵常数为6.2埃的立方晶体相的电子衍射照片时,从310的衍射强度高,我立即想到这是-Mn结构,而很快也就证实了。 高合金耐热钢中,除了合金碳化物外,还会出现一些中间相,如现在大家熟知的sigma相Laves相等。我研究了它们生成的合金化规律,在1953年写了一篇“Ternary Laves and sigma-phases in transition metals”在Acta Metallurgica上发表(Vol. 1, p.720)。当时,sigma相的结构研究甚嚣尘上,原因有二。一是FeCr sigma相首先是Bain(即贝氏体的发现人)在1925年在18-8不锈钢中发现的,由于它的析出,晶界贫铬而不耐腐蚀而且变脆。但是,用X射线粉晶谱标定一直未成功。加之高温合金那时已普遍受人重视,sigma相致脆是焦点之一。二是-U与sigma相有相似结构,战后正是和平利用核能大发展时期,对-U的研究正方兴未艾。sigma相的四方点阵直到1950年才定下来,我那时也凑了些热闹。sigma相的410和330是强衍射,一共有12个,因此显示伪12次对称。Nissen等就是在FeCr合金中首先发现12次对称准晶的。因为CrNiSi及VNi合金都生成sigma相,因此分别让王宁及陈焕研究它们,结果是陈焕在VNi及VNiSi合金中发现12次对称准晶,而王宁却扑了个空,没有发现12次对称准晶。幸运的是,他无意中第一次发现八次对称准晶,意义更大。科学研究就是如此,意想不到的往往是更大的发现。假如什么事都是预料到的,就不会有发现和发展了。 Laves是瑞士籍矿物学家,因为他在三十年代后期确定了C36-MgNi2晶体结构,并找出它与C14-MgZn2(六角)及C15-MgCu2(立方)结构间的关系,而后来统称这三种结构为Laves相。为了我的这篇文章Laves还给我写了一封信。不过,鲍林对这些结构称之为Laves相大为恼火,因为C14-MgZn2及C15-MgCu2结构是他的学生Friauf在1928年首先确定的,因此他后来称这些合金相为Friauf-Laves相。Laves相中有2/3的原子处于二十面体中心,据此我让董闯在具有C15结构的MnNiSi合金中找二十面体准晶,很快就找到了。 我提到上面说到的一些四十年前的往事,主要是想说明科学研究的积累和继承性。只有积累多了,才可能有所发现。不可能在没有扎实的基础的前提下建起高楼,更不可能一步登天。作学问就得肯下笨功夫,不能取巧,更不能急于求成,要有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精神。储备不多,机会来了也抓不住,或者是昙花一现。灵机一动是有的,但这也只是在已做了大量思索的情况下才会出现。 我在Uppsala几年都是使用X射线粉晶谱做合金相分析,为了弥补我在单晶体X射线衍射方面知识的不足,我在1955年11月下旬去荷兰Delft城的皇家理工学院跟W.G. Burgers教授做白锡到灰锡的相变。他是金属物理方面特别是金属范性形变的专家,有一些位错的问题搞不清楚。他在美国教水力学的哥哥J.M. Burgers回荷兰度暑假,W.G. Burgers就向他哥哥请教。他哥哥没用多久时间就搞出那篇以伯格斯回路和伯格斯矢量闻名于世的文章,不过此后他再也没有做过有关位错的工作。这位神童25岁就当了教授,与同年龄的学生喝酒吵起来,一拳把那学生打倒。教授打学生,天下少有,一时传为奇闻。1985年我去荷兰访问时,荷兰科学院的教授还津津乐道此事。不过,W.G. Burgers教授却是一位温文尔雅的学者,为人和蔼可亲。为了区别他们哥俩,哥哥被人称为聪明的Burgers,弟弟就成为笨Burgers,其实他并不笨,只是不如乃兄聪明就是了。白锡是金属,灰锡是金刚石结构,类似半导体,白锡在-13 C转变为灰锡。欧洲教堂中的风琴的乐管都是用锡做的,有一年冬天特冷,白锡中长满了黑斑(灰锡)并且由于体积膨胀而脆裂,称为Zinnpest,Zinn是德文的Tin,pest是黑死病,可译作锡疫。我长出白锡单晶,低温转变成灰锡,再用劳厄法研究两者的取向关系,1956年3月完成一篇论文。这桩工作本身意义不大,但我从中学到一些有关单晶的知识,如劳厄衍射带,这对日后的电子衍射工作很有帮助。但是我却不知道就在这所大学的物理系里,Le Poole前几年已把Boersch在1937/1938年就证明了的电子透镜的Abbe成象理论用于实践,通过改变中间镜电流可以聚焦在后焦面得到电子衍射图或聚焦在像面得到电子显微像。后来西门子EM1电镜在1953/54年投产,就有了选区衍射功能。现在,这已是尽人皆知的事了。 Delft是一小城,运河纵横,风车牧牛,一派田园风光。荷兰人很热情,这几个月我过得很快活。就在那里我在1956年3月看到周总理“向科学进军”的动员令,兴奋不已,4月底就乘机经苏联回到阔别九年的祖国。 |
3楼2009-05-28 09:54:39
Platinum
木虫 (正式写手)
- 应助: 2 (幼儿园)
- 贵宾: 0.1
- 金币: 2219.3
- 红花: 3
- 帖子: 383
- 在线: 96.6小时
- 虫号: 134481
- 注册: 2005-12-15
- 专业: 凝聚态物性I:结构、力学和
|
四. 初步涉足电子显微学 1954年我又回到了斯德哥尔摩,暴君Hultgren已退休,我继续在皇家理工学院开展高合金钢的研究。本来工程物理系的O. Linde也申请此教授位置,而此人是第一个有序结构AuCu3的发现人之一,在金属物理界赫赫有名,但是Hultgren说此人不懂冶金,培养不出钢厂要的工程师,利用在钢铁界的影响应是把这位学者挤下去,选一个学问不大由钢厂来的工程师继任。学术界的权术哪里都有,有学问的人不一定都被重用。 我在这时除了碳化物析出外,还研究铁素体的转变,(奥氏体)+M6C或Laves/sigma相。需要使用电子显微镜,就到附近的金属研究所使用瑞典唯一的RCA电镜。那是战后第一代电镜,只有一个聚光镜,消像散靠机械移动在物镜极件周围的八个小铁块来实现,没有衍射功能。但是我还是用复型观察到共析物的细节,写了两篇不锈耐热钢过烧的文章。薄膜制样方法还未出现,只能做胶膜复型,1953年R.M. Fisher发展出萃取复型,大约在1954/55年才有了碳膜复型。我用胶膜(萃取)复型观察到几十埃大小的VC颗粒及针状Mo2C,这是V、Mo在钢中产生晶粒细化及析出硬化(或二次硬化)的原因,1956年写了一篇文章,这是用电镜进行这类研究工作的早期著作,同时还有Seal在英国Sheffield大学及A. Schrader在西德马普学会钢铁研究所做类似工作。也就是在这一时期,我读了苏联科学家Pinsker写的由墨尔本学派(J.M. Cowley为首)译成英文的“电子衍射”一书。 我1953年夏去德国参观Schrader的工作,1955年11月初去英国Shefield大学参观了Seal的碳复型工作,顺便去了剑桥大学游览。那时Whelan已经用西门子EM1观察到铝中位错的运动,也可能做了不锈钢中层错与不全位错的工作,失之交臂,终生遗憾。如果那时见到他们的工作,说不定我就会改变主意,去剑桥大学的卡文迪什实验室工作一段。一头扎进晶体缺陷中去,可能也不会有后来的准晶研究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机会总是存在的,不要总是因为失去一次而懊悔不已,悲观失望,以致失去后来的机遇。 1951/52年我在杂志上见过Anna Chou在剑桥大学冶金系在Nutting指导下做的电镜工作(稍后G. Thomas在那做了铝合金沉淀过程的研究,用的是Al2O3复型)。回国后才知道她就是李林,用的她先生邹承鲁的姓。李林可能是中国第一个用电镜研究合金的人,她用的电镜说不定就是Nutting作为战胜国的专家在二次大战后去德国把尖端仪器作为战利品拆运回英国的,我在1964年见到Nutting,他跟我讲过这件事。不过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德国人砌了一道墙把一台西门子电镜藏到夹缝里,终于把这一台古董留下来,现在在柏林技术博物馆中展览。桥本初次郎在1960年在剑桥大学冶金系进修一年,是李林的师弟,他1978年第一次来中国一下飞机就找Anna Chou,谁也不知道这是哪一位,后来幸亏了解内情的柯俊解了围,他50年前后在英国,知道桥本找的就是李林。柯俊在伯明翰大学用光学显微镜观察过过热和过烧的钢的脆断断口上有硫化物的枝晶,证明有沿奥氏体晶界熔化现象。葛庭燧、柯俊和我近来都被日本金属学会选为荣誉会员,但是他们一直为不能准确分辨葛(Ke),柯(Ko),及郭(Kuo)三个字的发音而苦恼,在美国多年的晶界专家石田洋一(Ishida)还戏称我们为3K党。 当时西门子EM1是最好的配有衍射功能的电镜,日本的JEM5等才出来,不能望其项背。光是剑桥大学就购进8台,为开拓衍衬技术立下了头功。二十多年后JEM200CX出来,挤掉西门子EM102的市场,被迫停产。不怕后进,就怕不进。 |
4楼2009-05-28 09:55:19
Platinum
木虫 (正式写手)
- 应助: 2 (幼儿园)
- 贵宾: 0.1
- 金币: 2219.3
- 红花: 3
- 帖子: 383
- 在线: 96.6小时
- 虫号: 134481
- 注册: 2005-12-15
- 专业: 凝聚态物性I:结构、力学和
|
五. 望洋兴叹,读书自娱 薄膜衍衬技术是1955年兴起的,由于它能把晶体空间与衍射空间的信息结合起来,非常有生命力,很快就在全世界蓬勃开展起来,广泛用于晶体缺陷和相变的研究。1965年P.B. Hirsch等写了那本被Cowley(见Diffraction Physics一书中的序言)称为Yellow Bible的“薄晶体透射电子显微学”作为十年来工作的总结。五位作者都是皇家学会会员,这是前所未有的,一时传为美谈。 这个时期我已回到国内,看到人家电镜工作如火如荼的开展,我们守着几台苏联生产的落后电镜,开始时还心急如焚,后来也就逐渐变得麻木了。剑桥学派最令人佩服的还不仅是他们一流的实验工作,更是他们用运动学与动力学电子衍射计算出的模拟像与实验结构符合良好。差距越拉越大,后来索性也不去想它了。 中国第一台电镜其实是英国Metropolitan Vickers生产的。解放后在物理所工作的钱临照先生接到通知说,南京仓库里有原国民党政府交通部(也管电台)买的几箱设备,派何寿安去了解才发现是一台电镜,喜出望外。后来他们用这台电镜观察了铝单晶中交滑移在表面上产生的迹线。1953年钱三强率中国科学院代表团去莫斯科买回了几台苏联生产的仿战前西门子的电镜。1954年民德总统皮克送给毛主席一台Zeiss静电透射显微镜,安装在物理所。1962年金属所安装了一台民德的磁透镜电镜,也不高明。 大跃进前国内曾引进一批日本JEM6,JEM7,JEM150,H10,H11电镜,分辨率都不错,但是因为没配有双倾台,而国内又无力自己研制,衍衬工作还是不能真正开展起来。不过选区衍射的工作可以做了,聊胜于无。 我在这期间,除了安排些X射线漫射的研究课题外,主要是写一些电子衍射几何的教材(文化大革命中给一些青年人讲了讲,还被批判为对抗“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和阅读一些有关合金结构的文章。主要是Frank及Frank-Kasper以及Pauling学派关于四面体密堆相的论文,获益匪浅。 Frank早在1952年在讨论液体结构时就指出,等径钢球堆在一起得出配位数为12的多面体有三种可能性:一是面心立方密堆结构,二是六角密堆结构,三是二十面体(二十个正三角形围成的多面体有12个顶点,我在1986年见到Frank时,他告诉我德国一位原子物理学家早在30年代曾用二十面体作为原子核中质子堆集的模型)。前两种结构是常见的密堆结构,其中除了四面体间隙外,还有体积较大的八面体间隙。后一种密堆结构只有四面体间隙,因此堆垛密度最高,从原子对的Lennard-Jones势来看也最低。此外,它与前两种密堆结构相比,对称性最高,也最接近球对称。不过,这种二十面体密堆结构具有五次旋转对称,与点阵的周期平移对称不相容,因此只能存在于液体、非晶态、小粒子、生物大分子当中。在具有平移对称性的晶体中,二十面体单元一定要略加畸变才能相容。后来A.L. Mackay也在1962年讨论了这个问题及五次旋转对称,同时指出二十面体两个顶点间的距离比中心到顶点的距离长约5%。如果用等径钢球堆砌,在顶点上的12个钢球不能两两相接。换句话说,二十面体的表面要有裂隙。但是在两种元素构成的合金中,如一种原子的半径比另一种小10%,则小原子居于二十面体中心,稍大的原子落在定点,正好满足二十面体的几何要求。如MnAl12相,略小的一个Mn原子在中心,稍大的12个Al原子在顶点上,构成一个二十面体单元,这些MnAl12单元再放在一个体心立方点阵上,就是MnAl12结构。Mackay后来还在1982年进一步研究了二维及三维的五次对称晶体学并得出五次对称的光学衍射图,它是第一个堂而皇之的把五次对称引入晶体学的。Frank和Mackay可以说是五次对称的先驱,在实验观察到五次对称之前就预见其存在,令人钦仰。Mackay还独立地推导出夹角为72及36的菱形单元,此即所谓的Penrose块。此人是一大杂家,可借助计算机把英文译成中、日、朝鲜文,在科研上有不少创见,但无系统著作。撒切尔首相为了紧缩教育研究经费让一部分人提前退休,Mackay就榜上有名,1984年发现准晶后,他不但保住了职务,还晋升为教授,并选为皇家学会会员。如果准晶的发现推迟一年,他已提前退休,就不好圆场了。 Kasper是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的晶体学家,专门研究合金结构,他首先提出四面体密堆相中配位数为12(二十面体)、14、15及16的多面体。所有四面体密堆相都是由这些多面体单元堆砌成的,只是数量及方式不同而已。Frank有一年在西班牙(曾被阿拉伯人长期占领)看到的正方形、五角形、六角形套在一起阿拉伯图案,得到启发,把四面体密堆相的多面体结构分解成一些单元层,而这些层中原子就坐落在这些多边形连在一起的网络顶点处。他们把这些结果在1958及1959年在Acta Cryst.上发表,成为这方面的经典著作。美国物理学家,特别是哈佛大学的Nelson学派,称这些结构为Frank-Kasper相。其实这些合金相的晶体结构大都是化学大师鲍林和他的学生Friauf,Bergman,Samson及Shoemaker夫妇测定的。因此,鲍林很不服气,在一次大会上大叫,不应称这些为Frank-Kasper相。不公平的事在科学史上是屡见不鲜的。而这种偏见则是由于物理学家和化学家间彼此不了解造成的。 C. Frank可能是幸运儿,除了上面讲的外,还有Frank位错,Frank-Read源等。此人还很早晋爵,称之为Sir Charles(英国王室与贵族只能称名,不能称姓。无独有偶,中国的皇帝也是如此,如末代皇帝溥仪,很多人不知他姓爱新觉罗)。不过,那不首先是因为他在科学上的贡献,而是在二次世界大战中破译德国人的军事密码。据说丘吉尔首相(兼剑桥大学Chancellor,不管事的名誉职务)找Vice Chancellor(实质是管事的校长)要他推荐两个聪明的年轻人去搞密码,其中之一就是Frank博士。根据传统,英国的内阁首相不是剑桥就是牛津的名誉博士。撒切尔是牛津大学化学系的硕士,有人提议牛津大学给她荣誉博士学位,结果被教授会(Senate)否决,因为她削减科研经费。1989年我去牛津,Whelan带我参观,路过Senate会堂时说“我投了反对票”,不无自豪之感。 鲍林凭直觉“破译”了不少晶体结构,其中最出名的就是Mg32(Al,Zn)49。他在体心立方点阵的顶点上先放一个空心的二十面体,再在20个三角形上放20个原子构成有十二个正五角形的五角十二面体;再在这12个正五角形中心上放12个原子就构成由30个菱形构成的三十面体;每个菱形的两个三角形上放2个原子共60个原子就构成一个由正五角形和正六角形的有如C60一样的多面体,有如足球一样;再在正五角形及六角形上放一个原子就构成大三十面体;所有这些壳层都满足五次对称要求。这些大三十面体的体心立方排列就是Mg32(Al,Zn)49的结构。用这个模型计算出的X射线衍射强度与实验观察结构相符。这真是一篇绝妙佳作,发表在1957年Acta Cryst. 中。 这些不朽之作读起来赏心悦目,回味无穷,并且给人以启发。欣赏之余,不无感慨。当时读书是为了自娱,消磨文化大革命中的辰光,没想到后来还能派上用场。书到用时方很少,临阵磨枪是来不及的。知识面广,才能触类旁通,顺手引来,为我所用。不过不能读死书,完全相信文献中的记载,不敢越雷池一步。只会钦慕前人的成就,不敢和不会创造性的应用,发扬光大,也是没有出息的。 |
5楼2009-05-28 09:56:10
Platinum
木虫 (正式写手)
- 应助: 2 (幼儿园)
- 贵宾: 0.1
- 金币: 2219.3
- 红花: 3
- 帖子: 383
- 在线: 96.6小时
- 虫号: 134481
- 注册: 2005-12-15
- 专业: 凝聚态物性I:结构、力学和
|
六. 卷土重来,更上一层楼 1978年后,先是恢复研究生招生,接着是科学技术变成了生产力,我们再度酝酿引进新的电子显微镜。这一年,分别以藤本及桥本初次郎率领的两个日本电子显微学访华团来访,吹了不少HREM的风,接着1979年诺贝尔讨论会选中了HREM作为主题。这样,科学院就决定引进两台JEM200CX高分辨电镜,一台放在沈阳金属所,一台放在北京物理所,在1982年安装就绪。后来中国科技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等先后引进近10台JEM200CX,不过大都是分析型的样品台。 当时我从四面八方召来的研究生不少都集中在沈阳这台JEM200CX上做高分辨工作,从合金、半导体、氧化物、催化剂、矿物到有机化合物什么都做。后来逐渐集中到Frank-Kasper相上,一则样品易得,二则结构花样多,三则中年骨干叶恒强及李斗星先后到美国ASU大学,比利时Antwerp大学,瑞典Lund大学学习,熟悉这方面的工作,在Frank-Kasper相的畴结构方面出了一些好结果。接着王大能在1984年夏获得突破性进展,在高温合金中分离出来的Laves相,相及C相的单晶衍射图中都发现有五次对称分布的强斑点。这些Frank-Kasper相结构都是由二十面体柱的不同方式平行排列产生的。高分辨像说明这些Frank-Kasper相的纳米微畴犬牙交错地生长在一起,尽管它们的取向不同,它们中的二十面体柱都有相同取向。电子衍射图中五次对称分布的衍射斑点就是这些二十面体的傅氏变换结果。八月里我们写了一个摘要,寄到美国,准备由我1985年元月在庆祝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一百周年的HREM会议上宣读(由于我在1985年元旦患支气管炎住院治疗而未去)。同时准备写一稿子投Ultramicroscopy,在85年元旦后寄出。 在此工作启发下,想到如把这些合金相加热到熔融再急冷可能会得到更小的二十面体原子簇,于是安排了张泽做(Ti,V)2Ni合金,蒋维吉做ZrNi合金。到84年11月,张泽就得出了五次对称电子衍射图,为了进一步弄清整个倒易空间的情况,决定让他在85年春节去南京探亲期间去上海硅酸盐所,用那里的有双倾台的JEM200CX做大角度倾转实验,等他在二月里得出结果时,我已见到Shechtman等在Phys. Rev. Lett. 84年11月12日一期上刊登的有关Al-Mn准晶的文章,并且托人带给在上海的张泽。我们的发现是独立的,并且是首次在过渡族金属合金中合成的,但晚了一步。法国人称它为China Phase。 蒋维吉也在急冷ZrNi合金中得到五次对称电子衍射图,仔细分析这是由ZrNi相的10次旋转孪晶产生的,就像Al13Fe4十次孪晶一样。高分辨像也显示五个夹角为36度的三角形拼在一起,每个三角形中像点都排列在一个整齐的正交二维点阵上,与准晶的高分辨像中像点呈非周期性的五次旋转对称分布迥然不同。这张高分辨像后来在很多地方刊出,作为五次孪晶的标准照,从另一角度证明五次对称准晶不是五次孪晶。 1985年3月底去日本仙台东北大学访问看到Hirabayashi他们拍的Al-Mn准晶的高分辨像。文章在2月26日投稿(仙台大学金属研究所科学报告),三月份刊出,可谓快矣!成果抢先在手,全世界公认这是准晶的第一张高分辨像,广为转载。那年秋天召开北京一起分析会议,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的Lawless(他的先人一定是无法无天的土匪)报道了他们发现的Pd-U-Si准晶。当我给他看我们的Ti2Ni结果时他大为吃惊,怎么在中国也能有这么新鲜的发现!我们发现准晶是系统研究Frank-Kasper相的必然结果,因此我1986年春在英国Bristol大学及法国Les Houches会议上作的报告题目都是“From Frank-Kasper Phases to Icosohedral Quasicrystal”,Frank当时对此很高兴。 在这次第一届国际准晶会议上见到准晶的发现人Shechtman,Cahn及Gratias,首先把五次对称及二十面体引入晶体学的A.L. Mackay,还有不少其它名流。头一个报告当然是Shechtman讲,他的第一张透明片就是美国应用物理杂志对于他们的准晶一文的委婉退稿信,“你们的文章内容不适于在本刊登载,请另投一金属刊物”。Shechtman对于这个软钉子耿耿于怀,所以广为宣扬,大有不搞臭JAP势不罢休之势。由此看来,退稿也不那么可怕,换一种杂志试一试就是了。Phys. Rev. Lett.的编辑独具慧眼,1984年10月9日接到稿件,11月12日就刊登出来。但是,这里也有一段插曲。 Shechtman及Blech(二人都是以色列人)研究航空用的高强度铝合金,想通过急冷使铝中固溶较多的Mn,Cr,Fe等合金元素产生固溶强化,无意中在1982年在急冷Al6Mn合金中发现五次对称衍射图。找到在美国国家标准局工作的J.W. Cahn(犹太人,原在MIT材料系当教授)请教,Cahn信口说这是五次孪晶,在金、银、金刚石、硅、锗中常见。可是许多现象还是解释不了。他们又请教法国CNRS的冶金化学研究所的D. Gratias(不知是否是犹太人?),此人晶体学基础很好,二十面体对称这个点子可能是他的。不过,这与传统晶体学的周期性相矛盾,他们迟迟不敢发表。直到1984年秋在Santa Barbara加州大学的理论物理中心召开的一次讨论会中,Gratias听到Steinhardt讲他们的理论计算结果,不但液体结构中近邻取向序是二十面体对称,固体也如是。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统一,一拍即合。Shechtman等10月9日投稿的标题是“有长程取向序而无平移对称的一种金属相”,11月2日Levine和Steinhardt投稿的标题是“准晶:一种新的有序结构”,第一次提出准晶这个名词,并且说这是准周期晶体的简称。为此,Steinhardt还接见纽约时报记者,以新闻发布方式公布此发现。我国近来也有用新闻发布会公布科学发现之事。科学要保持其纯洁性,就不应与新闻和商业搅在一起,否则,非乱套不可。这种事及弄虚作假的丑闻近来屡次在美国出现,欧洲大陆却很少,我们要择其善者而从之。 哈佛大学应用物理系Nelson等一直用Frank-Kasper相结构中的二十面体研究液体及非晶态结构,Steinhardt曾在那里进修,有此思想是有其根源的。而Mackay在1982年就用过准点阵这个词,并且与Steinhardt讨论过。但是Steinhardt在这篇论文中避口不谈Mackay的贡献,只是在他计算得出的五次对称衍射图的角注中说Mackay曾得出相似的光学变换图。看来其中不无不尊重别人劳动的科学研究道德问题。 七十年代以来急冷铝合金的研究还是想当普遍的,会不会有人在Shechtman等之前也曾观察到准晶而失之交臂呢?的确如此。印度的科学家早在1978年用电子衍射研究Al-Pd及Al-Mn-Ni合金时就观察到五次对称及准周期排列的衍射斑点,为跟踪追击。再就是加拿大铝公司的科学家在1984年发表的论文中报道了Al-Cu-Li合金中的五次对称衍射,草率地作了五次孪晶的结论。现在这些人在准晶研究中已默默无闻。这些事例说明,机会出现了,还有一个能不能及时抓住它的问题。对新生事物敏感与否是考验一个研究人员的第一位的问题,有人独具慧眼,有人有眼无珠,差别就在这里。 讲到五次孪晶就不能不提鲍林。前面已经指出,很多有二十面体单元的结构,特别是Frank-Kasper相都是鲍林和他的学生测定的(从Friauf(1928)到Bergman(1957)和Shoemaker夫妇、Samson(1957-1980))。鲍林还用四层二十面体对称壳模型确定了Mg32(Al,Zn)49的结构。可是,又偏偏是他,在准晶发现后,歇斯底里地反对准晶,一而再再而三地说这是五次孪晶,不是准晶。在Nature关于准晶的通讯中他用了“Nonsense”这个词,而在Phys. Rev. Lett.等杂志拒绝发表他的论文后他就在美国科学院院报上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鼓吹孪晶学说,因为院士有权不经审查在院报上发表任何文章。他怎么会走向自己的反面了呢?只有用“老来糊涂”几个字说明,他毕竟已是90岁的人了。他坚信晶体具有周期性一说,因此就不能接受五次对称,尽管他搞了一辈子的五次对称结构单元而且是贡献极大的人。我已年近70,也应引以为戒。 何伦雄在1988年在缓冷的Al-Cu-Co合金中找到有十棱柱体外形的十次准晶单晶,甚至有几个毫米长,这是第一个发现的稳定十次对称准晶。我当时就想,Al-Co及Al-Cu-Co合金别人早已研究过,说不定也遇到过这种稳定准晶。剑桥大学Cavendish实验室在五、六十年代曾经先后有十几名博士在W.H. Taylor指导下系统地用X射线研究过铝合金相。好的成套的结果都发表了,零星的解释不了的就留在故纸堆中,说不定其中有宝。于是我要Cavendish实验室主任A. Howie请我去那当访问学者(剑桥叫做Commoner),原说一学期,后来我说忙,减为两个月,最后我说那也不行,改为一个月。原来每个学院每学期请一定数目的Commoner(除了住房不花钱,还可在高桌上吃晚餐(学生只能在矮桌上吃),并免费携带友人就餐,还有一些其它特权)。我呆的时间少,等于这个名额没很好利用,学院不乐意。我在1990年春光明媚的五月到剑桥,真是美极了,偏偏五月是考试季节,Mackey说:“假如没有考试,五月的剑桥有如天堂一般”。这话对我是适用的,我住在丘吉尔学院,离Cavendish实验室和图书馆都不远,主要是翻阅那十几部博士学位论文,皇天不负有心人,终于在Hudd的有关Al-Co合金相的博士论文中找到他观察到五次对称X射线衍射的描述。当时就写FAX要马秀良做Al3Co合金缓冷研究,一年后他完成一篇AlCo合金准晶及近似晶体相的大作,发表在Metall. Trans.上。从故纸堆中找窍门,也就是文化大革命中批判的从文献缝中找题目,是不费力而讨好的事,就看你是否留心于此。 在丘吉尔学院闲来无事就去学院内的图书馆及展览室逛逛。乖乖!丘吉尔小学毕业时的评语是“太顽皮,不知上进”,简直要把他打进地狱,幸亏他是贵族出身,不念大学可去海军服役,照样可以爬上去(后来当上海军大臣和首相),就跟文化大革命时干部子弟参军一样。不过丘吉尔绝不是蠢才,给他写评语的老师倒可能是。图书馆中有几百本当年拿破仑的藏书,我指出上面有拿破仑非常喜爱的蜜蜂标记。Howie对我的“渊博”知识敬佩不已,其实我是看拿破仑和约瑟芬的恋爱一书中描写他们卧室中所有家具及用具都画有蜜蜂才知道这个典故的。顺便说一句,拿破仑不仅会打仗,还会写情书,他与第一任夫人约瑟芬间的情书属于世界名著,年轻人不可不看。 我在王大能、张泽取得突破后,先后在金属所与北京电镜室带领三十多个研究生横冲直撞,发现了一大批准晶合金及多种准晶结构。不少研究生因这方面有良好表现在读完硕士后就被人要去出国当博士生去了,如王大能、陈焕、董闯、周大顺、王曾楣、邹晓东、何伦雄等。张泽、王宁、张洪、李兴中做完博士论文再出去,他们的工作就比较系统,曾就明显。当时也是怕政策多变,耽误了青年人出国,能早放出去就早放出去。现在看来,如果何伦雄能稳住,念完博士再走,他现在的成就会更大些。游建强文章多出了名,在国内当了教授后,国外纷纷来请。这些学生的辛勤劳动使我国的准晶研究处于国际先进行列,我自1986年以来被人邀请在国际会议上做了二十多次特邀报告,其中值得一书的有诺贝尔物理奖获得人Santa Barbara加州大学理论物理中心主任R. Schrieffer教授请我在1987年10月去那参加准晶讨论会,杨振宁请我在1988年夏去香港参加第3届亚太物理学会议,1990年春日本金属学会聘请我为荣誉会员并作准晶报告。这些成绩与荣誉要归功于这三十多位青年人的刻苦钻研和辛勤劳动,我只是起了一些催生的作用。 我在1950年前后在国外搞了九年个人奋斗,在合金钢组织结构与碳化物研究方面进入了世界前列。不过,那时我是单枪匹马在国外战场上撕杀。四十年后的今天,我卷土重来终于又把中国的准晶研究推向世界前列。这次人多势众,又是在自己祖国的土地上建立这个赶超世界科学水平的前哨阵地,得到的慰籍和自豪也远非昔日可比。中国的希望,科学的未来,就寄托在这些青年人身上。 |
6楼2009-05-28 09:56:42
Platinum
木虫 (正式写手)
- 应助: 2 (幼儿园)
- 贵宾: 0.1
- 金币: 2219.3
- 红花: 3
- 帖子: 383
- 在线: 96.6小时
- 虫号: 134481
- 注册: 2005-12-15
- 专业: 凝聚态物性I:结构、力学和
|
七. 而今迈步从头越 回顾我这一生,在学术上只做了两件事。青年时单枪匹马地冲杀在合金钢结构的第一线,中间停顿了四分之一世纪,到了六十岁又重振旗鼓领着一批青年占领了准晶研究的制高点。我并非才智过人,理论基础也不好(念大学时学潮频繁,微积分只学了微分,普通物理只学了力学和声学),又无特殊实验技巧(没有亲自改装过任何仪器),只是凭着一股追求真理的热情,在学科上从化工先转到冶金,再转到晶体学和材料科学,在实验技术上从金相转到X射线又转到电子显微学,一直契而不舍地拼搏,才能有一些收获。执著地追求真理,这是一个科学工作者首要的精神。 其次,我也充分利用和发挥了我在业务上的长处。我在合金学、晶体学、电子显微学三方面都懂一些。尽管在每一方面我都算不了专门家,甚至可能是半吊子,但是综合在一起我却能做到那些专门家做不到的事,也就是31/3>1。这也就是杂交优势。奉劝青年人,不要把自己的业务范围搞得太窄,画地为牢,不敢越雷池一步。也不要怕改行,生怕丢掉自己那一点看家本事。人生一世,还是多接触一些行当为好。学科交叉才能产生交叉学科,一个人要多懂几门学问才有出息。 再其次就是要有敢于创新的精神。有些人很有学问,讲起课来层次分明,写文章广征博引,就是科学研究没有新意,出不了前人的圈套。他的学问都是从别人那里贩来的,还没有变成自己的。西方强调教育与科研要结合,这是有道理的。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教书不只是再重复和向学生灌输知识,而是启发学生思考问题。因此,光是博学还不够,还要学以致用,要别出心裁。我们的准晶就是因为不与别人雷同,才能每年有新花样。晶体对称理论专家A. Janner每次见到我都要问我有什么新结果,他说他们搞理论的就靠吸收营养(新实验结果的启发)才能有所发展。王宁发现了八次准晶,Janner做了理论分析,写了篇大块文章。不过,也有人不这么看,如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材料科学系的G. Shiflet教授曾不无讽刺地说“理论家就是从我们材料科学家那拿去我们的想法,做一番理论分析,就是他们自己的了”。再就是加州理工学院应用物理系的W.L. Johnson教授曾说:“我们那只有基本粒子才认为是纯正高尚的物理,我们搞离子束与物质的作用被认为是低级物理(原文是dirty physics),但是这些理论家的研究全无新意,而我们在Phys. Rev. Lett.发表的文章比他们多”。这些都说明理论与实践的统一问题在世界各个角落里都存在。 再有一点就是充分相信青年中蕴藏着极大的创造性,放手让他们去实践。我经常有二十多个学生,采取放羊式领导。东方不亮西方亮,哪一点亮了就给予支持鼓励,照亮一片。谁出了头就让谁出国深造,这一招比什么仙丹妙药都灵。现在不少人培养研究生有如农村生产队的队长,每天早上上工时分配工作。研究生绝对超不过老师的水平,怎又能青出于蓝胜于蓝?王宁、陈焕发现八次准晶,何伦雄等发现一维准晶,李兴中最近用彩色群处理二维准晶对称,都是他们自己闯出来的。当然,我对学生还是很严的,高标准要求,毫不含糊。古人云:“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只有高标准要求才能激励青年人的进取心。反过来,这对青年人也有好处,身搞四、五篇论文,不愁没人来请,结果是我的学生过半数得到国外资助出国深造。最近四年,王宁、张洪、朱敏、李兴中四位博士都申请到德国洪堡奖学金。德国Jülich核研究院Urban教授先后要了五个我的学生和助手去那工作。这些都说明这里培养的青年人还是有国际竞争力的。有人说这是“胡罗卜加大棒”,只要能有胡罗卜吃,挨几大棒也是值得的。 最后,我认为我之所以在回国后学术上无所作为达二十五年之久(实际上是几起几落,多次遭到只专不红,脱离实际,竺春花式人物的批判,只因为我欣赏越剧艺人竺春花说的“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地做戏”),并不懊丧,在机会到来时能抓住不放,猛冲上去,还是因为我们这个年纪的人青少年时饱受帝国主义欺凌,民族意识强,爱国之情深。我小学是在哈尔滨念的,九一八后逃到天津,在南开中学念书,七七事变后又逃到重庆。有一阵子天天夜里逃空袭,有一枚日本炸弹就在几十米外爆炸,灼热的泥土在我身上烧伤的疤痕至今犹在。在1944年底在遵义浙江大学念到四年级时,日本骑兵一千多人从柳州横冲直撞几百里一直打到贵州的独山,我又从贵州逃往四川,这些烙印是几十年时间也不能磨灭的。80年我在离开瑞典二十四年后又回到那里,见到当年在一起搞科研的老朋友,他们都是上层人士,不是经理就是教授,有人问我回国后经历多次政治运动,学术上无甚成就,后悔不后悔?我说不后悔,因为我是与我国人民一起经历这些折腾的。如果我这几十年不在国内经受这些考验,我不会有这份爱国爱人民的深情。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悠久历史,是世界上唯一连绵未断又古又新的文化,这是值得我们每个中国人骄傲的。个人损失了二十几年的科研生涯,比起上下五千年,这又算得了什么?就是这股力量激励我前进,要在有生之年,把中国的电子显微学搞上去,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就在这个关键时刻,科学院领导批准我们引进一台200KV场发射透射电镜,还配有Gatan Image Filter系统,加上我们原有的五台电镜及各种附件,我们的仪器装配可以说是世界一流的了。在93年聘请了八位海外优秀青年电子显微学工作者回国短期或长期工作的基础上,今后准备进一步扩大这种合作,传播新的学术思想,掌握新的实验技术,开展新的研究课题,在本世纪内把中国的电子显微学研究推到国际先进行列中去! |
7楼2009-05-28 09:57:28
8楼2009-05-28 10:17:48
lwp1017
木虫 (正式写手)
- 应助: 0 (幼儿园)
- 金币: 1475.7
- 散金: 40
- 红花: 6
- 帖子: 684
- 在线: 57.7小时
- 虫号: 466006
- 注册: 2007-11-23
- 专业: 电工材料特性及其应用
9楼2009-05-28 17:30:07
10楼2009-05-28 17:33: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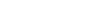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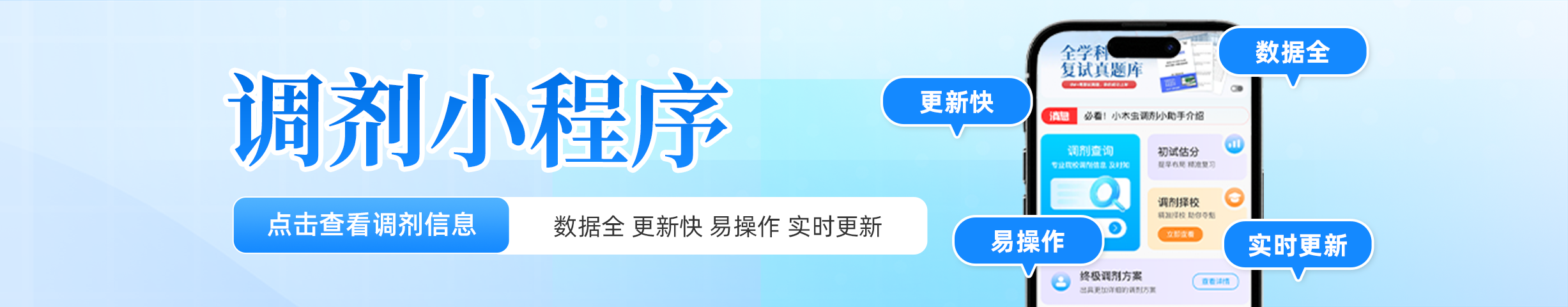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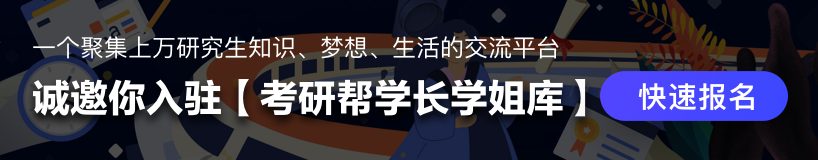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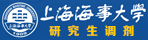



 回复此楼
回复此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