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查看: 779 | 回复: 2 | |||
| 当前主题已经存档。 | |||
xylang金虫 (正式写手)
|
[交流]
科研体会(朱棣文)(2)
|
||
|
可是这篇文章只开创了一个摸索前进的方向,此后两年间还要通过 玻 恩(M. Born , 1882 - 1970)、 狄拉克、 薛定谔(E.Schrdinger , 1887 - 1961)、玻尔等人和海森伯自己的努力,量子力学的整体架构才逐渐完成。量子力学使物理学跨入崭新的时代,更直接影响了二十世纪的工业发展,举凡核能发电、核武器、激光、半导体元件等都是量子力学的产物。 1927年夏, 25岁尚未结婚的海森伯当了莱比锡(Leipzig)大学理论物理系主任。后来成名的布洛赫(F. Bloch , 1905 - 1983,核磁共振机制创建者)和特勒(E. Teller , 1908 -,“氢弹之父”,我在芝加哥大学时的博士学位导师)都是他的学生。 他喜欢打乒 乓球,而且极好胜。第一年他在系中称霸。1928年秋自美国来了一位博士后,自此海森伯只能屈居亚军。这位博士后的名字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周培源。 海森伯所有的文章都有一共同特点:朦胧、不清楚、有渣滓,与狄拉克的文章的风格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读了海森伯的文章,你会惊叹他的独创力(originality), 然而会觉得问题还没有做完,没有做乾净,还要发展下去;而读了狄拉克的文章,你也会惊叹他的独创力,同时却觉得他似乎已把一切都发展到了尽头,没有甚么再可以做下去了。 前面提到狄拉克的文章给人“秋水文章不染尘”的感受。海森伯的文章则完全不同。二者对比清浊分明。我想不到有甚么诗句或成语可以描述海森伯的文章,既能道出他的天才的独创性,又能描述他的思路中不清楚、有渣滓、有时似乎茫然乱摸索的特点。 三、物理学与数学 海森伯和狄拉克的风格为甚么如此不同?主要原因是他们所专注的物理学内涵不同。为了解释此点, 请看图1所表示的物理学的三个部门和其中的关系:唯象理论(phenomenological theory)(2)是介乎实验(1)和理论架构(3)之间的研究。(1)和(2)合起来是实验物理,(2)和(3)合起来是理论物理,而理论物理的语言是数学。 ┏━━━━━┓ ┃ 实 验 ┃ (1) ┗━┯━┯━┛ ┏━┷━┷━┓ ┌ ┌ ┃ 唯象理论 ┃ (2) │ 玻尔 | ? ┗━┯━┯━┛ │ 海森伯┤ ↑ ↓ │ └ ┏━┷━┷━┓ 爱因斯坦 ┤薛定谔 ┃ 理论构架 ┃ (3) │ ┌ ┗━┯━┯━┛ │ │ ↑ ↓ │ 狄拉克 ? ┏━┷━┷━┓ └ └ ┃ 数 学 ┃ (4) ┗━━━━━┛ 图2 几位二十世纪物理学家的研究领域 海森伯从实验(1)与唯象理论(2)出发:实验与唯象理论是五光十色、错综复杂的,所以他要摸索,要犹豫,要尝试了再尝试,因此他的文章也就给读者不清楚、有渣滓的感觉。狄拉克则从他对数学的灵感出发:数学的最高境界是结构美,是简洁的逻辑美,因此他的文章也就给读者“秋水文章不染尘”的感受。 让我补充一点关于数学和物理的关系。我曾经把二者的关系表示为两片在茎处重叠的叶片(图3)。 重叠的地方同时是二者之根,二者之源。譬如微分方程、偏微分方程、(Bob注:原图是仅在底部少量重叠的两个长卵形叶片) 希尔伯特空间、黎曼几何和纤维丛等,今天都是二者共用的基本观念。这是惊人的事实,因为首先达到这些观念的物理学家与数学家曾遵循完全不同的路径,完全不同的传统。为甚么会殊途同归呢?大家今天没有很好的答案,恐怕永远不会有,因为答案必须牵扯到宇宙观、知识论和宗教信仰等难题。 必须注意的是在重叠的地方,共用的基本观念虽然如此惊人地相同, 但是重叠的地方并不多, 只占二者各自的极少部分。譬如实验(1)与唯象理论(2)都不在重叠区,而绝大部分的数学工作也在重叠区之外。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重叠区,虽然基本观念物理与数学共用,但是二者的价值观与传统截然不同,而二者发展的生命力也各自遵循不同的茎脉流通,如图3所示。 常常有年青朋友问我,他应该研究物理,还是研究数学。我的回答是这要看你对那一个领域里的美和妙有更高的判断能力和更大的喜爱。爱因斯坦在晚年时(1949年)曾经讨论过为甚么他选择了物理。他说: 在数学领域里, 我的直觉不够, 不能辨认那些是真正重要的研究,那些只是不重要的题目。而在物理领域里,我很快学到怎样找到基本问题来下功夫。 年青人面对选择前途方向时,要对自己的喜好与判断能力有正确的自我估价。 四、美与物理学 物理学自(1)到(2)到(3)是自表面向深层的发展。 表面有表面的结构,有表面的美。譬如虹和霓是极美的表面现象,人人都可以看到。 实验工作者作了测量以后发现虹是42高漫楚A红在外,紫在内;霓是50高漫楚A红在内,紫在外。 这种准确规律增加了实验工作者对自然现象的美的认识。 这是第一步(1)。进一步的唯象理论研究(2)使物理学家了解到这42侦P50升i以从阳光在水珠中的折射 与反射推算出来,此种了解显示出了深一层的美。再进一步的研究更深入了解折射与反射现象本身可从一个包容万象的麦克斯韦方程推算出来,这就显示出了极深层的理论架构(3)的美。 牛顿的运动方程、麦克斯韦方程、爱因斯坦的狭义与广义相对论方程、狄拉克方程、海森伯方程和其他五、六个方程是物理学理论架构的骨干。它们提炼了几个世纪的实验工作(1)与唯象理论(2)的精髓,达到了科学研究的最高境界。它们以极度浓缩的数学语言写出了物理世界的基本结构,可以说它们是造物者的诗篇。 这些方程还有一方面与诗有共同点:它们的内涵往往随□物理学的发展而产生新的、当初所完全没有想到的意义。举两个例子:上面提到过的十九世纪中叶写下来的麦克斯韦方程是在本世纪初通过爱因斯坦的工作才显示出高度的对称性,而这种对称性以后逐渐发展为二十世纪物理学的一个最重要的中心思想。另一个例子是狄拉克方程。它最初完全没有被数学家所注意, 而今天狄 拉 克 流 型 ( DiracManifold)已变成数学家热门研究的一个新课题。 学物理的人了解了这些像诗一样的方程的意义以后,对它们的美的感受是既直接而又十分复杂的。 它们的极度浓缩性和它们的包罗万象的特点也许可以用布 雷 克(W. Blake , 1757 - 182 7)的不朽名句来描述: To see a World in a Grain of Sand And a Heaven in a Wild Flower Hold Infinity in the palm of your hand And Eternity in an hour 它们的巨大影响也许可以用蒲柏(A. Pope , 1688 - 1744)的名句来描述: Nature and nature's law lay hid in night: God said, let Newton be! And all was light. 可是这些都不够,都不够全面地道出学物理的人面对这些方程的美的感受。缺少的似乎是一种庄严感,一种神圣感,一种初窥宇宙奥秘的畏惧感。我想缺少的恐怕正是筹建哥德式(Gothic)教堂的建筑师们所要歌颂的崇高美、灵魂美、宗教美、最终极的美。 (Bob注:原文有大量注释和引用文献略) 【原载《二十一世纪》第40期】 治学体会(杨振宁) 作者:杨振宁 1938年2月,我们家到了昆明,我在当年秋天进了西南联大,在西南联大念了4年本科、两年硕士。这6年时间,在我一生的学习历程中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我曾多次回想过这段时间,我觉得我得到了西南联大师生努力的精神和认真的精神的好处。 1945年我到美国芝加哥大学念博士学位。当时芝加哥大学的物理系是全世界最有名的,我之所以选芝加哥大学最主要的是因为费米教授在那里执教。费米教授是20世纪一位大物理学家,也是历史上最后一位又会动手,又会做理论研究的大物理学家,他在这两方面都有第一流的贡献。1942年他在芝加哥大学主持建造了世界上第一个核反应堆。人类利用自然界的能源最早是火,后来也用水。1942年费米所领导的核反应堆,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芝加哥大学当时是人才济济。费米教授1954年得癌症去世了,他死时才53岁。另外有位非常重要的物理学家,当时只有三十几岁,叫做泰勒。泰勒现在还健在,已经80多岁了。我在芝加哥大学做学问的时候,泰勒已经是位很有名的物理学家,后来更有名了,人们称他为“氢弹之父”。在芝加哥大学的两年给了我另外一个非常好的训练。 我常常回想我在芝加哥大学的训练和我在昆明西南联大的训练。在我一生的研究过程中,这两个训练最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而且是不同的影响。 在西南联大的学习,给我的物理学打下了了非常扎实的根基,我把这种学习方法取名叫演绎法。什么叫演绎法呢?就是从大的原则开始,从已经了解的、最抽象的、最高深的原则开始,然后一步一步推演下来。因为有这个原则,所以会推演出结果。比如说热力学第一定律、热力学第二定律。这个推演的方法,如果你学得好的话,可以学习前人已经得到的一些经验,一步一步把最后跟实验有关系的结果推演出来,这样可以少走弯路。 到芝加哥大学以后很快就发现,芝加哥大学物理系的研究方法跟昆明的完全不一样。费米和泰勒他们的注意点不是最高的原则,这并不是说他们不懂最高原则。这些是已经过去的成就,他们不会忘记,可是这些不是他们眼中注意的东西。他们眼光中随时注意的东西常常是当时一些新的现象,而他们的研究方法是先抓住这些现象,然后从这些现象中抽出其中的精神,可以用过去的基本的最深的原则来验证。我把这取名叫做归纳法。 归纳法常常要走弯路,因为你是在探索,所以你走的方向往往是错误的。比如说,泰勒教授是个热情洋溢的人,他早上到学校里来,走到走廊上立刻抓住一个人,不管这个人是教师还是学生,他说昨天晚上他有一个很好的想法,于是就把他的想法讲出来。过了一个钟头,他碰到另外一个人,他就讲另外一套理论。所以我说,泰勒教授一天大概有十个新想法,其中有九个半是错的。可是你想想,假如一个人每天都有半个正确的想法,他的成就就会不得了。这一点给了我很深的印象,因为这个办法跟我在昆明学的,跟从前我在北京小学、中学里学的是相反的。怎么说相反呢?就是在中国传统的教育体制下(我知道在今天的中国教育体制下,这个办法还是很普遍的)。你要在你的脑子里分清什么东西是你懂的,什么东西是你所不懂的,不懂的东西不要去沾它,你要沾的东西是懂的;然后来了一个老师,拉着你的手,走到一个你还不懂的领域里,一直到你完全懂了为止。这是中国从前的传统的教育哲学,也是今天儒家传统影响之下的东亚国家的教育传统。对这个传统,大家知道有名的一句话,所谓“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个办法有没有好处呢?有很大的好处。我之所以在昆明有很好的底子,原因就是受了这个教育哲学思想的影响。它可以让你少走弯路,使你一步一步地、完完整整地把一门学科又一门学科学好。 我刚到美国的时候很惊讶,美国的学习方法不是这样的。刚才我讲泰勒教授常常有很多新的想法,其中很多是错的,而他不怕把他错误的想法讲出来。他跟你讨论的时候,如果你指出他的想法有什么缺点,他很快就会接受;然后通过跟你的讨论,这些想法就会更深入一层。换句话说,他对于他不完全懂的东西不是采取害怕的态度,而是面临它、探索它。这个对于我有很大的启发。我在1948年得到博士学位以后,在芝加哥大学留校做了一年博士后,那时候叫教员。在那一年之中,我参加系里每周一次的讨论会,参加讨论会的人有费米、泰勒、尤里。尤里是20世纪的大化学家,他是发现重水的人。还有梅尔跟梅尔夫人,他们两位都是非常重要的化学家和物理学家,还有几位别的人,人才济济。在这个讨论会上,整个的气氛是探索的气氛。我记得这个讨论会常常没有固定的题目,大家坐着喝咖啡,谈谈有什么心得或新来的消息。我深深地记得我最早的一篇文章就是在这个讨论会上受到启发写成的。有次讨论会上泰勒说,他听说在伯克利有人发现了有所谓不带电荷的π质子,而且这个π质子会衰变成两个光子;他又说这可以证明这个质子自旋是零。于是在座的人就问他怎么证明,他就给出了一个证明在黑板上。但这个证明很快就被我们打倒了,大家指出他的证明没有想清楚,想得太快。可是当天晚上回去后,我想他这个证明虽然不完全,可是却走了第一步,再走两步不仅可以得到他所讲的结论,而且可以得到更新的一些结论。所以过了几天,我就写出了一篇文章。这只是一个例子。 另外,我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我从泰勒教授那里,也可以说无意中学到了一个做学问的方法。我在昆明的时候,念过量子力学,量子力学大家知道是物理学中的一门基础课,我念的是王竹溪教授所教的。他教得非常全面,而且也非常之深,我还留有王竹溪先生教的量子力学笔记。这笔记是用很粗糙的草纸记的,比现在的手纸还粗糙得多。这些笔记至今我有时候还要看,因为那上面有些公式我现在还要用。到了芝加哥大学,泰勒开的一门课也是量子力学,我又去重选了。泰勒非常之忙,所以他通常不备课,讲课的进修有时就会误入歧途。我那时对量子力学已经有相当多的认识,所以当他误入歧途时,我知道他就要出问题了,这对于我有很大的启发。因为当他发现他要出错的时候,他一定要想法赶快弥补,当他想法弥补时,思想就像天线一样向各个方向探索到底是什么地方走错了。那么,在这关口,如果你对这个题目是很了解的话,你就可以看出来他在物理学上的想法:他注意什么,不注意什么;哪些真正是他心里觉得值得注意的,哪些只是雕虫小技,是不重要的。通过这点我也学到了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像费米、泰勒这样的物理学家,他们对物理学的价值观念是什么,在这方面我受到了很大的好处。所以在十几年以前,在我60岁的时候,我在香港中文大学做了一个演讲,在演讲时我说我非常幸运。因为我在中国时是在中国传统教育哲学的影响下,得到了其中最好的精神;在美国,我又在一个截然不同的教育哲学影响之下,得到了其中最好的精神。我是两方面都得到了最大的好处,这是我非常幸运的地方。 1949年夏天,我从芝加哥大学去了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这是世界有名的研究学府,里面没有研究生,教授也非常之少,大概一共二十几人,其中研究物理的四五个人,研究数学的七八个人,剩下还有几个研究历史的,研究考古学的。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跟普林斯顿大学没有关系,这两个机构都在同一个小镇上,是两个完全独立的机构。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最有名的人当然是爱因斯坦。我在普林斯顿的时候, 爱因斯坦已经退休了,不过他每天还到他的办公室去。当时物理方面有三四个博士后,我是其中之一。我们都不太愿意去打扰这位我们都非常尊重的老物理学家,不过他有时候作的演讲我们都去听,那时候我已经结婚了,有一个孩子。在孩子4岁时,有一天我带他走到一条路上。我知道爱因斯坦每天都走这条路到他的办公室去,我把他截住了。我问:“爱因斯坦教授,你可不可以和我的孩子合个影?”他说:“当然可以。”所以,我就照了一张像,这张像一直保存在我们家庭的相本里。 我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前后呆了17年,这17年是我一生中研究工作做得最成功的17年,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有很多非常活跃的、从世界各地来的、工作最好的年轻人。我们有激烈的讨论、激烈的辩论,也有激烈的竞争。 到1965年,我的一位朋友叫做托尔,比我年轻两岁,他也是念理论物理的,他曾是马利安大学物理系的系主任,他把马利安大学的教师阵容从20余人发展到100多,他的行政能力是很强的。1965年,纽约州的长岛成立了一所新的大学,叫做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所以就请他做了非常年轻的校长。他对我说,希望我也到石溪去,可以帮助他一起创建一所新的以研究工作为主的大学。这对我,不是轻易能作决定的,因为刚才我讲过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的17年,是我研究工作做得很出色的年代;而且在普林斯顿可是说在世外桃源,没有这样那样的委员会,也不需要教课,可以每天用百分之百的时间做研究。不过考虑了一段时间以后,我答应去那里。为什么呢?因为那时我40岁出头,我了解到,人生不只是研究工作,可以把普林斯顿比做一个象牙塔,可是在世界上不只是在象牙塔里,在象牙塔之外还有很多重要的事情,包括教育年轻人。我把这点相清楚以后,就同意到石溪去了。 到现在我在石溪也有29年了。在这29年间,我所主持的一个物理研究所有许多的博士生毕业,他们都是我的学生,还有一些在研究方面有一些成就的同事,也是我的学生。另外我们有很多的博士后,这些博士和博士后都纷纷到世界各国去了。美国有一个很好的体制,就是一个学校的毕业生,学校不一定留他做教师(在国内我觉得没有努力向这个方向去做)。博士后做得很好的毕业生,我们通常也不留他。我们的博士和博士后分散在世界的各个地方,他们都建立了他们的新的影响以及收了他们自己的学生。这个办法有很大的好处。 因为每个研究所都有它的气氛,有它的注意方向,也可以说有它的价值观,学生分散到各个地方去,可以增加彼此观摩、彼此学习的机会。 常常有同学问我,说我们将要得到博士学位,或者我们正在做头两年的博士后,我们应该做什么样的题目,是大题目呢还是小题目?这个问题很重要,而且我在做研究生的时候,也问过费米。费米的回答很清楚,他说,他觉得大题目、小题目都可以想,可以做,不过多半的时候应该做小题目。如果一个人专门做大题目的话,成功的可能性可能很小,而得精神病的可能很大。做了很多的小题目以后有一个好处,因为从各种不同的题目里头可以吸取不同的经验,那么,有一天他把这些经验积在一起,常常可以解决一些本来不能解决的问题。这一点,我自己就有很深的感受。 |
» 猜你喜欢
 博士自荐
已经有6人回复
博士自荐
已经有6人回复
 博士推荐
已经有4人回复
博士推荐
已经有4人回复
 求环氧树脂研发1名
已经有10人回复
求环氧树脂研发1名
已经有10人回复
 280求调剂
已经有5人回复
280求调剂
已经有5人回复
 什么是人一生最重要的?
已经有10人回复
什么是人一生最重要的?
已经有10人回复
 面上可以超过30页吧?
已经有13人回复
面上可以超过30页吧?
已经有13人回复
 为什么中国大学工科教授们水了那么多所谓的顶会顶刊,但还是做不出宇树机器人?
已经有13人回复
为什么中国大学工科教授们水了那么多所谓的顶会顶刊,但还是做不出宇树机器人?
已经有13人回复
 版面费该交吗
已经有17人回复
版面费该交吗
已经有17人回复
 【博士招生】太原理工大学2026化工博士
已经有8人回复
【博士招生】太原理工大学2026化工博士
已经有8人回复
bird007
荣誉版主 (职业作家)
踩单车的季节
- 应助: 10 (幼儿园)
- 贵宾: 6.35
- 金币: 17460.5
- 散金: 5019
- 红花: 48
- 沙发: 1
- 帖子: 4641
- 在线: 656.1小时
- 虫号: 21919
- 注册: 2003-08-29
- 性别: GG
- 专业: 凝聚态物性 II :电子结构

2楼2005-12-07 01:27:21
3楼2005-12-07 09:16: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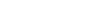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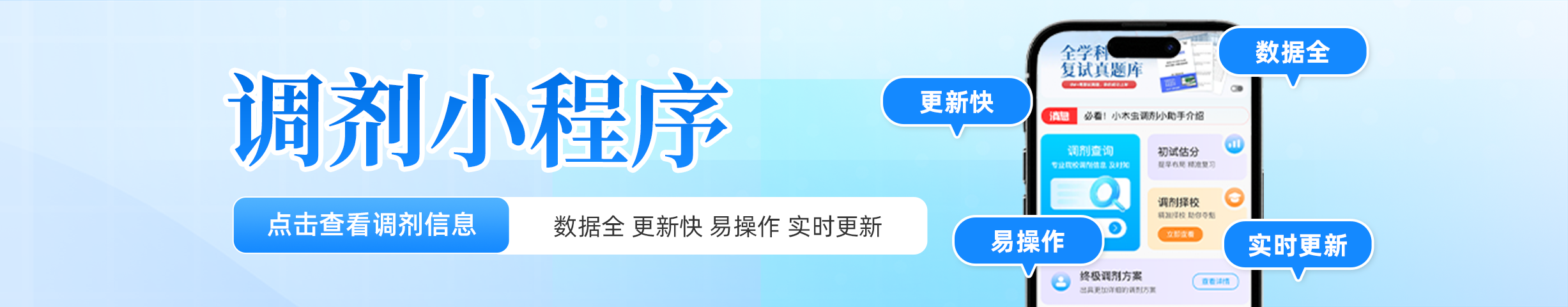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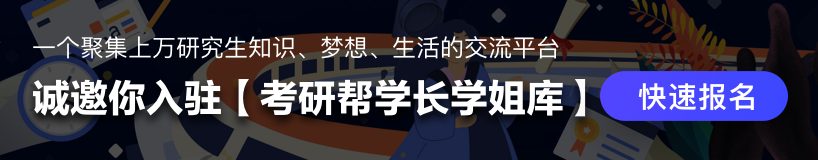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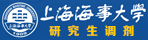



 回复此楼
回复此楼